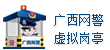以“自然之子”審視生存之境
□ 薛臣藝
一個涼爽的夜晚,我和黃其龍在燈光迷蒙的邕江邊散步。他突然告訴我,他的首部散文集即將出版,并口頭承諾等書出來后,要送一本給我。對此,我很是期待。他之前在文學期刊上發表的那些散文,大部分我已拜讀,自認為他用心打磨出來的那些“有難度”的散文非常適合集中展現出來,從而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文學效果。
黃其龍的《空間:貓、硅膠工廠和心脈》這部散文集出版,已過一段時間了,也沒見黃其龍主動送書給我。礙于面子,為了不驚擾他,我沒向他討要。直到一位編輯約我寫一篇《空間:貓、硅膠工廠和心脈》的書評,我才提醒他,我還沒有他的新書,評論寫不出來。他向我解釋,他手頭的100本樣書賣的賣(簽名本),送的送(主要送給他的母校),少部分已被人索要,如今一本都不剩了。最后,他就近索回一本借給我看看,等我看完了再把書還回去。可見,《空間:貓、硅膠工廠和心脈》這部散文集還是頗受歡迎的。
書到我手上之后,我從頭到尾認真研讀,并沒有因為再次閱讀而感到“審美疲勞”,反而越讀越興奮,頻繁用鉛筆在一些精彩的句子下面畫橫線。考慮到這本書已有主人,我不得不強迫自己一次又一次將鉛筆放到桌面上。
黃其龍散文創作的一大特點是,語言表達能力很強,喜歡夾敘夾議,富有質感,有一種很立體的感覺,似他家鄉崇左的花山巖畫那般神奇,突兀中盡顯古樸,好像能穿越古今那般。說得通俗一些,有點像他所屬的民族——壯族的五色糯米飯,好看又好吃,內涵豐富,象征意義較強。比如,《蜜蜂飛來飛去》最后一句,“我說,好的,替我照顧他,讓他剝離孤獨。”蜜蜂能照顧守在寂寥鄉村的年邁祖父嗎?在黃其龍看來,勤懇且正義,一個人抽著煙罵那些“進行毀滅式獵取”獵蜜人的祖父也需要精神上的慰藉。飛來飛去的蜜蜂能夠給祖父帶來熱鬧、金錢和療愈,讓卑微的生命獲得輕盈的姿態,以對抗生命長河中的孤獨感。從中也可以看出,他對蜜蜂的喜愛與感激,對祖父的美好祝愿以及一絲絲個人無法在祖父身邊盡孝的無力感與羞愧感。
在書中,他時常寫到孤獨與熱鬧。在《火燒云少年》里,他徹底道出了自己的孤獨。那是父母親為了賺錢不得不連夜遠赴廣東打工而把他留在老家的辛酸,那是父親患上肺癌四十出頭就離世帶給他永久的痛,那是他在廣東的硅膠工廠艱難謀生的命運寫照。當然,目睹了彩姨男人的死之后,作為小孩的“我”也感到很孤獨,那是無力抵抗和愛莫能助的孤獨。面對收入微薄和買商品房的高額付出,“我”亦感到十分孤獨。這是物質貧困導致的血淋淋現實和心理壓迫。黃其龍并沒有回避人生的困頓,在生存的艱難中,通過率性地書寫直面一個又一個問題,讓人感同身受,對“命運”一詞有了更具象的理解。
黃其龍顯然受到存在主義哲學的影響,《空間:貓、硅膠工廠和心脈》一書有不少關于生存之境的探討。在《空間:貓、硅膠工廠和心脈》這篇作為書名的文章中,他欣然寫道:“我想到我的憂慮和恐懼促使我通向存在時,才談得上自我選擇的自由,那時候,我的那些空間才是打開的,與光明與閑適相聯,一個人剛從娘胎里掙脫到現實世界,首先要承受的是恐懼和不安,才有后來不斷涌現的新奇與快樂。”這樣的見解無疑是清醒與樂觀的,寫出了人對絕望的反抗。這樣的哲學本色、哲學智慧一直貫穿于書中,更容易引起讀者的思考,獲得一種精神上的認同感。
在首篇《川上的婚姻》中,黃其龍提到了“熱鬧”一詞。他是這樣寫的:“我也喝了一大口下去,氣氛突然熱鬧起來。”看到這里,我終于松了一口氣,仿佛跟他一樣,心情變得開闊起來,忘掉了種種急促與不安,不再擔心“禮金的問題、婚禮消費的問題”。這些“熱鬧”來自人與人之間的真誠與善意,來自母親對兒子那種毫無保留的親情之愛。這是對抗孤獨的一劑良藥。
此外,置身大自然,也是黃其龍對抗孤獨的一大法寶。他說,他超喜歡大自然,我則稱他為“自然之子”。《空間:貓、硅膠工廠和心脈》一書有很多精彩的自然環境描寫。在《深深藍》中,他動情地寫道:“沒有什么比離開城市去到鄉野追蹤鳥類的足跡更令我和瑾感到歡愉了。”生活在南疆,典型的喀斯特地貌讓他領略了自然之美,也賦予他“堅硬的內質”,使得他敢于一次次突破圍困他的牢籠與有別于他人的散文寫作,形成了個人鮮明和獨特的寫作風格。
在書中,黃其龍多次寫到繪畫、音樂、舞蹈等藝術對他所產生的影響。藝術讓他獲得心靈上的愉悅,這也是他對抗孤獨擺脫孤獨的情感寄托,彰顯了藝術對人生的凈化與提升功能。
黃其龍不屬于“講故事”的寫作者,他充分運用意識流的寫作手法,在時空的不停轉換中,盡力展現他的生存之思。我喜歡《南方多芭蕉》的巧妙構思,通過不同地方遇見的芭蕉串聯起全文,把“自由聯想”的寫作手法運用到極致。我也期望他今后把筆觸更多地伸向“他者”,寫出更多像《人潮漫卷》這樣關注他人的文章來。一旦走出“自我”的天地,世界就會變得更加廣闊,散文寫作也就變得更有趣,像大海那般容納更多的東西。
(本文作者系廣西作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