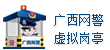那朵花兒那些年
□ 歐 志
網(wǎng)上偶然查到,“夢特嬌”商標(biāo)上那朵小紅花,原來是虞美人。這名字讓我愣了愣,既關(guān)聯(lián)著法國文化里的浪漫優(yōu)雅,又暗合“霸王別姬”里虞姬的決絕,恰似我與這個品牌糾纏的二十多年,藏著太多細(xì)碎的時光印記。
故事要從一件亮絲T恤說起。20世紀(jì)九十年代初,我在縣城工作,見領(lǐng)導(dǎo)干部和企業(yè)家們常穿進(jìn)口夢特嬌,筆挺滑順,領(lǐng)口那朵小金花在陽光下閃閃爍爍,像別著一枚體面的勛章。單身的我心頭發(fā)癢,咬咬牙花1200元買下一件5號蘋果綠。那是我第一次觸碰“奢侈”二字。包裝袋一打開,一股清冽的化纖芳香彌漫開來,像摻了巴黎的風(fēng);吊牌上的鐳射標(biāo)識最是神奇,不同角度晃一晃,那朵花便在光里變幻出虹彩,據(jù)說是當(dāng)時最頂尖的防偽技術(shù);洗水標(biāo)上的一組數(shù)字,被售貨小姐稱為“法國出生證”。
衣服是真好看。大翻領(lǐng)口配三顆奶白紐扣,像把星星別在了頸間;左胸口袋上,一根枝條托著三片葉子,頂起一朵金色五瓣花——那時我們都叫它“小標(biāo)花”。穿在身上清爽得很,面料滑溜溜的不貼身,連皺紋都懶得生。我對著鏡子轉(zhuǎn)了又轉(zhuǎn),覺得自己也有了幾分“領(lǐng)導(dǎo)范兒”,走在街上總?cè)滩蛔⊥χ毖澹杏X路人投來的目光像溫水,虛榮心被泡得發(fā)脹。只是這滑溜也添過尷尬:束衣角時,褲頭總墜著BB機(jī)和手機(jī)往下滑,得趁人不注意偷偷提一把,手心捏著汗,臉上還得裝作若無其事。
那時,我不過是個普通工薪族,1200元的T恤已是極限。褲子是菜市場買的普通西褲,皮鞋一百多元,手腕光溜溜的,沒名表,脖子上更沒有老板們常掛的金鏈子。可這件T恤像塊磁石,讓我對所有帶虞美人標(biāo)志的東西著了魔。后來的幾年,我成了家人眼里的“夢特嬌癡漢”:皮鞋、襪子、襯衫、夾克、手提包、皮帶……從腳到頭,但凡印著那朵花,總想法子買到它。它們多是國產(chǎn)的大眾款,不再是奢侈品,可摸著布料上熟悉的紋路,就像握住了一點安穩(wěn)的歡喜。
2000年去香港,在商場瞥見一件粉紅色夢特嬌T恤,心跳忽然漏了半拍。499元買下時,手心沁著汗,這是葡萄牙產(chǎn)的真絲款,沒口袋,左上胸繡著朵醒目的大虞美人,胸前三道白杠像給衣服系了條輕快的絲帶。那時我身材偏瘦,穿上正合身,束衣角再也不墜褲頭了。同事見了總夸“顯年輕”,追問在哪兒買的,我嘴上含糊著,心里卻像揣了顆糖。
第一件蘋果綠T恤,陪了我五六年。洗衣時沒講究,總往太陽底下曬,蘋果綠慢慢褪成灰白,后背洇出大片汗?jié)n,像潑了墨的山水畫。我把它塞進(jìn)衣櫥角落,直到某天在街上撞見有家染衣店。80元染成酒紅色那天,我捧著衣服像接回個老朋友,唯獨胸前的虞美人被染成了暗紅,失了往日金亮,像蒙了層霧。同事們圍著夸“新衣服真精神”,我嗯嗯啊啊應(yīng)著,指尖劃過那朵褪色的花,忽然懂了:有些體面,終究是留不住的。
染過的T恤穿了兩年,酒紅漸褪,紅中帶灰,差不多打回原形,舍不得丟棄,被我送回老家給大哥。“這可是進(jìn)口貨,新買時1200呢。”我話音剛落,就被他數(shù)落“敗家”。可沒過多久,他放牛時總穿著它,跟同村大爺們念叨:“你們摸摸,這料子,一千多呢!”眾人不信,伸手捻捻,嘖嘖稱奇:“這么舊了還這么滑溜,抓一把都不起皺!”直到某天他上山打柴,被樹枝鉤破兩道絲,正應(yīng)了那句“亮絲不怕火,就怕鉤”,那兩個小洞像給衣服打了個句號。大哥后來打電話時還在懊惱:“多好的衣服,被我糟踐了。”我聽著,忽然笑了:一件進(jìn)口衣服能陪人放牛、打柴,才算真的在中國活過。
這些年見多了夢特嬌的仿品。越南芒街的商店里,150元的“正品”用火機(jī)燒著演示,老板拍著胸脯比劃,可那朵虞美人繡得歪歪扭扭,一看就露了餡。也記得新聞里說,有中國游客帶假夢特嬌在法國機(jī)場被罰款。可對我來說,真假早不那么重要了。就像大哥那件破了洞的舊T恤,哪怕商標(biāo)掉了、絲斷了,也比任何仿品都珍貴。
如今再看見夢特嬌的虞美人,總想起那朵蘋果綠T恤上的小金花。它曾陪我走過縣城的街,陪大哥放過牛,在歲月里褪過色、重染過、破過洞,卻把細(xì)碎的歡喜、尷尬、不舍,都釀成了酒。這朵藏在時光褶皺里的花,早不是什么品牌符號了,它是面鏡子,照見過年輕的虛榮,也映著日子的實在。
風(fēng)一吹,仿佛又聞見那股清冽的化纖氣息,像二十多年前那個午后,我第一次打開包裝袋時,陽光正好落在那朵虞美人上,亮得讓人睜不開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