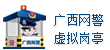有鳥鳴湖
□ 宋揚
每天清晨上班前,我都繞道一公里去鳳翔湖聽鳥。鳳翔湖位于小城新區十多年前新建起的一個濕地公園的核心區。湖心有一小洲,長約十來米,寬三米左右,洲上有一棵很大的黃葛樹。這個湖并沒有開發游船項目,人跡不至,洲便成了絕對意義上的孤洲。洲上鳥極多,鳥類卻單一。兩三百只鶴占據了這一塊諾亞方舟式的寶地。鶴中純白的居多,一飛起來,頗有“毛衣新成雪不敵,眾禽喧呼獨凝寂”的意境與規模。“獨凝寂”是相對于麻灰色的鶴而言,那些“少數派人士”糾正了我認為這種體型的鶴都是白鶴的錯誤認識。
小洲無名,我自個兒把它叫作“鶴島”。在湖的其他區域,我見過的鳥不下十種,小型的如麻雀、翠鳥等,中型的有畫眉、白頭翁、斑鳩……甚至更大一些的灰鷹也出現過幾次。然而,這些鳥都上不去“鶴島”。“白鶴亮翅”“鶴舞白沙”,鶴在文學意象中唯美、清雅,但從“鶴島”十多年來不曾被其他鳥兒染指看來,鶴群固守領地也相當強勢。或許,幾只散兵游勇般的鶴在兇悍的大鳥眼中不堪一擊,但當鶴以集團軍的陣勢盤踞于樹梢作死守之態時,再強大的攻城方也可能要掂量一下“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代價。當然,也有可能那些偶爾從鳳翔湖上空高高飛過的大雁和老鷹們,壓根兒就不屑垂眼一望這個小洲。在高傲的它們眼里,這只是一塊不值得覬覦的彈丸之地。
沒有目睹過這群鶴與其他鳥的戰爭,上述文字便只是想象與推測。說“這群鶴”,似乎并不準確,因為“群”的概念只基于它們都是鶴科而已。單說白鶴與灰鶴,它們顯然就不是同一家族的近親。遠了幾代?答案根本無從考證。如同我們這群從四面八方奔赴城市定居的人,或攜妻帶子,或素昧平生。一個個家庭匯聚成整個龐大的社會,各種關系把我們錯綜復雜地扭結在一起。那些鳥,也應當屬于不同族群,至少屬于不同家庭。
無論是清晨、上午、中午,還是下午、晚上,“鶴島”幾乎沒有絕對安靜的時候——哪怕三五分鐘。有一天,我深夜去了“鶴島”。那一次,我從夜里十一點待到凌晨兩點。那晚,初夏的夜風有些微涼,風攜帶了湖水淡淡的魚腥味,和著“鶴島”上鳥糞絲絲縷縷的臭,以及野生鳥類身上與生俱來的無以言說的酸騷,一陣陣迎面吹來。大自然如此雜亂而粗拙,腐爛氣息讓我想要立即逃離。但強忍一會兒后,我竟然感覺那些復合的氣息似乎有些新鮮,我竟然有些迷醉于那種新鮮的感覺。我知道,大自然從來都不只是溫馨、唯美的,正如純藍的天空中也有飛鳥墜落,潔白的雪山之巔也有羚羊被禿鷲啃光的骸骨。我們以為的大美之境,卻可能是有些生物的殞命之處,而我們眼中的窮兇極惡之所,卻可能是另一些物種的福地。每一個物種都有最合適它存活的地方。
那一夜,我聽到“鶴島”傳來鶴們音量、音長、音高層次分明而駁雜繁復的聲聲啼鳴。我屏息斂聲地聽,從駁雜中分辨出輕輕的“咕咕”聲,像籠中的鴿子,猜測那大概是鶴中長者在召開家庭會議并進行語重心長的叮囑;又聽出有些倉皇的哀鳴,比受驚的鴨群發出的“嘎嘎”聲更尖利一些。旋即,樹冠在一團朦朧的模糊中突然一陣猛烈抖動,急速扇動翅膀的“噗噗”聲此起彼伏——料想是打斗的鶴正在奮力保持身體平衡……
“鶴島”上的鶴們在競爭中共生。這個島安謐而殘酷,但它正是以這樣的方式在這個地方創造并繁衍著生命。難怪英國博物學家阿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會說:“野生動物之間的相互競爭,最終導致了物種間或物種內部的相互合作,讓它們成為整個地球生態系統的一部分,最終形成和諧的統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