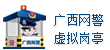院子的時光膠囊
□ 明素盤
童年的記憶像墨跡般洇在磚縫里,像一道永遠(yuǎn)愈合不了的細(xì)微傷口。那時,母親的白大褂常常晾在公共走廊的鐵絲上,隨風(fēng)輕輕搖晃。
手術(shù)室的謝姨走路總是很快,橡膠鞋底在水泥地上發(fā)出“吱吱”的聲響。她的手指修長蒼白,指甲修剪得近乎苛刻的短,仿佛隨時準(zhǔn)備伸進(jìn)某個生命的裂縫里。她的丈夫何叔在化工廠上班,身上總帶著一股刺鼻的酸味。他們很少同時出現(xiàn)在院子里,像兩個交替值班的麻醉師,一個醒來時,另一個必須睡去。
后勤的曾阿姨會收集番桃樹上掉落的果實,洗凈曬干后泡酒。酒液漸漸染上曖昧的粉色時,余叔叔就會喝上一杯。他喝酒時總是皺著眉頭,仿佛在品嘗某種可疑的藥液。他的聽診器永遠(yuǎn)掛在脖子上,金屬部分貼著胸口,漸漸染上體溫,像一塊長進(jìn)肉里的懷表。
梁叔一家是我的鄰居,他家的三個男孩總愛在院角的三角梅叢里鉆來鉆去。紫紅色的花瓣沾在他們的頭發(fā)上、衣領(lǐng)上,像一個個微型的淤血點。他們的母親玲如阿姨在門診部工作,每天要給無數(shù)陌生人量體溫、測血壓。但當(dāng)她站在走廊盡頭喊兒子們吃飯時,聲音卻總是發(fā)抖,仿佛面對自己親生的骨肉時,反而失去了職業(yè)性的冷靜。
記憶中那個笑聲如銀鈴一樣的陳姨是個美人,她走路有些跛,聽媽媽說,她是年輕時下鄉(xiāng)巡診時摔傷的。她的丈夫張叔叔在法院工作,說話時總帶著念判決書般的篤定。他常說要用鋼釘給妻子固定腿骨,陳姨就笑著搖頭,說身體里帶著金屬,下雨天會疼。他們的對話飄在晚飯后的院子里,混著各家各戶的洗碗聲,顯得那么平常。
媽媽原是手術(shù)室的麻醉護(hù)士,我常常看她仔細(xì)清洗雙手,指縫、指甲、手腕,一遍又一遍。有時半夜急診手術(shù)回來,她會坐在燈下補(bǔ)記錄,臺燈的光圈映著她疲憊的側(cè)臉,像浮在海面上的月亮。后來由于上夜班身體吃不消的原因,媽媽就調(diào)到了病案室管理檔案。記得小學(xué)放學(xué)后的大部分時光,我?guī)缀醵际窃趮寢尩霓k公室里做作業(yè),等媽媽下班后一起回家……媽媽有一本厚厚的麻醉記錄本,里面記滿了我看不懂的各種數(shù)字和符號。
谷倉的宿舍改建的窗戶又高又窄,陽光只能斜斜地切進(jìn)來,在地上畫出明亮的平行四邊形。我常常蹲在這些大大小小的光塊里,和我的小伙伴們無憂無慮地跳繩,看灰塵在光束中飛舞,像無數(shù)微型的生命在狂歡。母親說那是細(xì)菌,叫我離遠(yuǎn)些。但我知道,有些東西,越是被告知危險,越是誘人靠近。
院子的番桃樹開花時,整個院子都浸在粉色的霧靄里。花瓣落在公共水池邊,被水浸濕后變成暗紅色,像手術(shù)室里丟棄的紗布。曾姨的酒缸就放在樹下,酒面上浮著的花瓣漸漸失去顏色,像褪去的麻醉效果。
梁叔叔家的老二有一次從三角梅架上摔下來,前額劃了道口子。玲如阿姨抱著他往急診室跑時,血滴了一路,在水泥地上開出詭異的小花。后來那些血跡被沖洗干凈,但每次經(jīng)過那個地方,我總覺得能聞到淡淡的鐵銹味。
我們家搬走的那年,番桃樹開得特別盛。母親把她的麻醉記錄本打包進(jìn)紙箱,上面壓著幾件舊毛衣。爸爸把他的自行車、幾個大木箱子和皮革沙發(fā)整齊地嵌進(jìn)一輛小貨車上。谷倉高處的窗戶一格一格從車窗外退去,像被撕下的處方箋。父親單位的新宿舍并不寬敞卻有獨立的陽臺,還有幾平方米的袖珍衛(wèi)生間和只容得下兩個人的小廚房,媽媽和我說,搬到新宿舍,爸爸上班近,不用騎那么遠(yuǎn)的車回家了。
幾十年過去,谷倉還在,當(dāng)時的醫(yī)務(wù)大樓成了熱門的旅游景點,番桃樹和三角梅都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整齊的冬青。那天,我在原地站了很久,突然想起母親說過,麻醉最危險的時刻不是讓人睡去,而是如何讓人醒來。
如今媽媽已經(jīng)八十歲了。她迷上了各種樂器,每天都會有一小段屬于她的音樂時光。她的手指依然修長,只是像棵老樹般刻滿了歲月的痕跡,媽媽說自己就是一本寫滿注釋的舊病歷。有時電視里播放醫(yī)療劇,她會突然說:“當(dāng)年謝愛群可不是這樣打結(jié)的。”然后沉默,仿佛在回憶某個手術(shù)的細(xì)節(jié),又像是在確認(rèn)自己生命的縫合處是否依然牢固。
生命是什么?是母親麻醉記錄本上那些褪色的數(shù)字?是番桃酒里漸漸沉底的花瓣?是三角梅架上早已風(fēng)干的痕跡?或許生命就是這樣一個大院子,我們進(jìn)進(jìn)出出,留下一些紗布、酒精、體溫計,藥片……最終連自己的病歷也被歸檔到某個塵封的柜子里。在無人翻動的時間里,默默計算著麻醉與清醒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