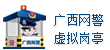白發(fā) 黑發(fā)
□ 侯東光
那把牛角梳,靜靜躺在母親的鏡匣里。梳齒間,纏繞著幾根銀發(fā)。晨光透過(guò)窗戶照進(jìn)來(lái),泛著柔和的光。
我一遍遍梳理著母親滿頭的銀發(fā)。銀發(fā)有些倔強(qiáng)地蓬松著,仿佛還帶著生命的溫?zé)帷N业氖种复┻^(guò)發(fā)絲,心里想著這些年來(lái),我們母子間那場(chǎng)心照不宣的“合謀”——一場(chǎng)關(guān)于黑與白的溫柔偽裝。
我是何時(shí)長(zhǎng)出白發(fā)的,已記不清了。只記得第一次在鏡中看到一抹霜白時(shí),心頭一緊。后來(lái)隨著年齡增長(zhǎng),白發(fā)滿了半個(gè)頭。倒不全是為自己,更多的是想到住在南寧武鳴哥哥家的母親,我每次回去武鳴看望母親之前,我都會(huì)仔細(xì)把白發(fā)染黑。我不是臭美、裝酷,我是想讓母親看見(jiàn)的,是一個(gè)精神矍鑠的兒子。讓她安心,讓她高興,讓她驕傲。這算不算一種最原始最樸素的孝道?
年過(guò)八旬的母親,何嘗不是一位更高明的“演員”。不知是從哪一次開(kāi)始,她迎接我時(shí),總會(huì)戴上一頂帽子,或是普通的毛線帽,或是輕薄的棉布帽,把她那滿頭的白發(fā)捂得嚴(yán)嚴(yán)實(shí)實(shí)。起初我沒(méi)在意,以為母親怕風(fēng)怕冷,后來(lái)才慢慢明白,她是怕我看見(jiàn)她滿頭的白發(fā),會(huì)擔(dān)心她、掛念她。讓我放心,就是母親樸素的愛(ài),最深沉的愛(ài)。
從防城港到南寧武鳴不到200公里的路程,成了我們母子演繹溫情的舞臺(tái)。我們每次相聚,都是一場(chǎng)精心準(zhǔn)備的“隱瞞”。我頂著一頭讓她心安的烏發(fā),她戴著一頂讓我寬心的帽子。我們聊著家常,聊著過(guò)去,聊著身體,卻都小心翼翼地避開(kāi)被刻意隱藏的真相。
直到11月5日,母親毫無(wú)預(yù)兆地卸下了她的行頭。她坐在一張矮板凳上安然睡去了,帽子放在一旁,那頭銀發(fā)終于毫無(wú)保留地展現(xiàn)在我眼前。我打來(lái)清水,用那把她用了一輩子的牛角梳,蘸著水,極輕、極慢地為她梳理。
我淚流滿面,心里反復(fù)念著:“媽,以后每次‘看’您,我還會(huì)把白發(fā)染黑……”
我知道,在那個(gè)沒(méi)有病痛的世界里,您一定等著看您的兒子。而您喜歡的,一定還是他年輕健康的樣子。那么,這場(chǎng)“偽裝”就還不算落幕。今后思念您的日子里,當(dāng)我對(duì)著鏡子把白發(fā)染黑時(shí),那不再是對(duì)衰老的掩飾,而是對(duì)您無(wú)聲的承諾!
黑發(fā),是為了告慰逝去的凝望。母親那一頭銀發(fā),是我心中永愛(ài)的印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