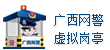不同顏色的石頭
□ 盤小春
不同顏色的石頭,在我的童年里占據著不同的位置,有的偶爾出現,未驚起心中的波瀾;有的看似平平無奇,卻早已在我的生命里留下痕跡。在故鄉白嶺,白色的石頭極為罕見,純白色的石頭更是寥若晨星。在大人眼中它們一文不值,但在我們的世界里,純白色的石頭是“奇珍異寶”,是快樂石。
夏日,晴天的中午或傍晚太陽落山的時候,約幾個小伙伴到村口的河灘上撿白石頭。這條河很小很小,小到中國地圖上沒有它的身影,桂林的地圖上也沒有它的蹤跡,就連村莊的示意圖里,它也只是一條細細的、彎彎的線條罷了。別看它小,但是它在故鄉人的心里又是很大很大的,大到可以和流向大海的長江、黃河,流經喀斯特地貌區的漓江,以及北去的湘江相媲美。
那時,我們喜歡玩“尋石”的游戲。游戲通常由撿到白色石頭的人先拿著石頭,其他幾人在河道邊站成一排,再由拿白石頭的小伙伴把石頭丟到前方的河道里,等漣漪散盡,丟石頭人說:“開始!”大家憑著記憶,以潛水的方式憋一口長長的氣,像一條條霓虹燈魚一樣潛過去找石頭。這個游戲考驗人的記憶力、肺活量、潛水的速度等等,誰先撿到白石頭誰就贏,再把石頭丟出去,繼續尋找,直到把白石頭玩丟在河道里,才依依不舍地上岸穿衣服回家。
粉色的鵝卵石是我的畫筆。童年的時候,我常到一條只有大暴雨時才有水流淌的小溪里玩,撿起粉色的鵝卵石,把它當畫筆一樣拿來畫畫。河岸邊不規則的大石塊,是我童年免費的畫紙,我玩到哪一河段,看中哪一塊,就在石頭上畫畫。秋天的稻穗,山上的毛栗子,是我作畫的意對象,我常將它們畫在石頭上裝點河岸。村里藏青色的石板路,也是我天然的畫板,我常到秋收后的田野里,撿起散落在田間的稻谷擺在石板上,對著它們想象和作畫。畫作中描繪了,一個小男孩趕著一群小黃鴨在田里覓食;夕陽西下,歸來的牛群,踩著石板路回家。童年的我非常向往的黑白電視、彩色電視……于是就用粉色的石頭在墻壁上畫滿了電視,電視里有雪花,有黑貓警長,樓頂上高高立起來的天線。
石灰巖是我的化學啟蒙老師。有一年秋天,村里種的稻谷收成不好,畝產量銳減,村民懷疑土質出了問題,于是自發組織到村邊的石頭山上打石頭燒石灰。起初是三五戶人燒石灰,后來越來越多的人加入燒石灰的隊伍。村民們分工合作,成年男子負責打石頭,以及把石頭運到村邊的一個廢棄的窯洞邊堆著。另一部分男子負責在石灰窯里壘放石頭,基礎做好后,將運來的石頭放入石灰窯里。婦女則負責上山砍柴,把它們挑到石灰窯洞口前面的荒田上。那年秋天,因燒石灰要大量的木柴,靠近村邊的山坡被砍得遠遠望過去,像剃了頭一樣干凈。
為減輕婦女們的負擔,老人跟著上山幫砍柴,湊熱鬧的小孩也去了。他們大擔小擔地挑著柴回來,長長的挑柴隊伍像一條長龍一樣沿著彎彎的小路從山坡一直連到石灰窯前……挑完柴的那天晚上,村民們圍在石灰窯前的田里,舉行了簡單的點火儀式,燒石灰就開始了。晚上圓圓的月亮掛在天上,亮堂堂地照在田野上。豐收后的田野,像鍍了一層薄薄的銀光一樣明亮。忠誠的小狗見到此情景,快樂地在田野撒歡,小孩們在這個稻草堆上躲躲,那個草堆上藏藏,玩著自己喜歡的游戲。
夜晚,村民圍坐在石灰窯前一邊添柴,一邊聊天,誰累了困了就在邊上的草堆上躺躺休息會兒,再起來換班添柴……烈火焚燒兩天后,石頭變了顏色,有些還裂開了,里面露出雪白的顏色,直到最頂層的石頭里面全變成了白色了,才宣布可以停火了。
關火,待石灰冷卻后,村民就開始分石灰了,你一擔,他一擔地分……我們家分了一擔,一百多斤,我們挑著石灰回家,把它們堆在墻角落里。
那年秋天,村民拿著新燒的石灰,撒在翻耕后的田里,白茫茫的一片,遠遠望去,如秋日里的晨霜,又如初冬時的薄雪那樣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