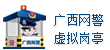山風過處是歸程
□ 韋炳旺
“突突突”,摩托車在山道上行進。
車子剛拐過竹林彎道,我就看見父親的身影嵌在榕樹的濃蔭里。“突突”聲尚未停穩,父親已拄著棗木拐杖站起身叫一聲“阿旺啊!”他揚手招呼的剎那,袖口滑落露出瘦骨嶙峋的手腕,腕上那串山核桃手串是我前年捎回的,如今已被盤得油光水滑。
我剛跨下摩托車,父親就拉我坐在青石板上,布滿老繭的手探過來撫上我的臉頰,說:“看看這臉色,比臘月里透亮多了,下頜線都圓乎起來咯。”他說話時,嘴里缺了半顆的門牙漏著風,卻把“圓乎”二字說得格外清晰。
回到屋里,父親從褲兜里摸出皺巴巴的煙盒,抖出支自卷的旱煙,邊點煙邊說:“不久前看到電視里說,西山鄉弄峰村那個支書栽了。危房改造款也敢伸手,你說這‘貪’字咋就長了腿?”他頓了頓,用煙桿敲了敲石凳:“我編了句順口溜——‘一人不廉,全家難圓;貪字頭上一把刀,隨時就要捅死人’,你聽聽在理不?”
我知道父親講這句話的用意。老父親雖只念過初中,卻當了山里“教書匠”,他的床頭總碼著《廣西日報》合訂本,墻角的舊彩電常年鎖定新聞頻道。
我接過父親的話說:“現在接待少了,體檢單上的箭頭都歸了位。”父親猛地拍腿站起來,拐杖戳得地面咚咚響:“早就該這么治了!有的人在酒桌上的一頓吃喝,可是山里一家人三季的口糧啊!”“你看這幾筐玉米粒……”父親抓起把玉米粒在掌心揉搓,“從翻地到脫粒,曬了五個大太陽,才攢夠兩千斤。你們一場酒吃掉的,是我和你娘彎數百次腰才換來的。”父親轉身盯住我,眼里布滿血絲:“你尿酸高,痛得站不起來時,我去鎮上抓藥,聽藥店老板說‘這病都是喝出來的’,你知道我心里是啥滋味?”
我必須改變。改變是從扔掉那雙锃亮的皮鞋開始的。當我第一次穿著解放鞋踩進幫扶村的稻田時,感覺步履多么輕松。如今,再翻開工作筆記,密密麻麻記著的是“藍家豬場需打疫苗”“李家茶園缺有機肥”等內容。有個月,暴雨沖垮了村道,我帶著村民扛沙袋加固河堤,肩膀磨出血痕時,一位七旬的大爺塞給我個烤紅薯:“干部能和我們在一起泥里滾,這路就能很快修好。”
離村時,父親往摩托車后座綁了袋剛磨的玉米粉,又塞進來一捆用野藤扎好的艾草。摩托車發動時,“突突”的聲浪驚起一群白鷺。我從后視鏡里看見父親仍站在山口,拐杖戳在地上,像插在泥土里的路標。山風掠過耳畔,恍惚間,又聽見父親在榕樹下的叮囑,那聲音混著泉水叮咚與秧苗拔節的輕響,在山谷間久久回蕩——那是一位九旬老人對土地的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