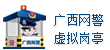家園的守望者
□ 審國頌
印象中我的第一位父親叫周友庭,他走的那年,我才6歲,至今已有30多個年頭了。
對于父親,弟弟和妹妹也許沒有什么印象了,就連我,能記得起來的,也僅是他又高又瘦的身子,還有那因為肺結核而沒日沒夜的咳嗽聲,至于臉,已經模糊得找不著輪廓了。
父親走的時候是一個夏天的傍晚,母親還在田里打谷子。父親一直病著,沒法做工,坐在家門口的曬坪上招呼著我和弟弟妹妹燒火、煮飯、喂豬、收曬坪上的谷子。那時同在屯里的堂弟剛好過來打酒——父親從不喝酒,但他為人隨和,朋友多,家里常來客人,常備酒。我提著家里的那壺酒給父親倒到堂弟拿來的瓶子里,一瓶酒沒倒滿,父親就歪倒到一邊去了。
我被突如其來的這一幕嚇慌了,抓著他又哭又喊,弟弟妹妹見了也跟著我哭喊,但他始終沒有回聲。母親那時剛好挑著一擔谷子牽著牛回到離家不遠的小坡上,一看到我們在曬坪上哭喊著,她丟下了谷子,牛也不拴就拼命地直往家跑。
當我們七手八腳地把父親抬進家的時候,他已經沒了氣息。因為我和大妹的號哭,小弟和小妹也跟著不停地哭。母親見了,喝住了我:“你還哭,你是老大你還哭那弟弟妹妹怎么辦!”我驚慌地停住了,可我分明看到母親滿眼滿臉都是淚水。
其實早在一天之前,父親讓母親把那套新一點的衣服洗了,趁太陽好曬一曬,母親就知道能和父親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了,只是她一直都沒說。父親雖然一直病了好幾年,但他人好,會打算,雖治病欠了不少債,但一家人都還算過得平安開心。只是父親這一走,丟下我們四個兄妹,母親一個人該如何擔起這擔子呀!
那時村里還沒通電,看著天色漸漸變暗,母親拉著我們幾個找來了兩盞煤油燈,把一盞點上,放在屋中間的方桌上,然后把另一盞和一盒火柴交給了我和大妹,說:“去北城把你們的舅公叫來,如果天黑了看不見路就點上燈慢慢走。”
母親說的北城是我們村與都安百旺鎮交界處的一個小屯,離我家約四五里路,舅公家就在那。
去北城的路得翻過幾個無人的山坡,那里有好多的墳墓,我心里很怕,但我不敢說,我擔心我一說,大妹也跟著怕了。
那晚,我拉著年僅5歲的大妹摸索著哭著跑了一路,跌倒了好幾次,爬起來接著跑。一直沒點燈,因為燈在我們跌倒時已經摔爛了燈罩沒法點了。后來,舅公和我們一起連夜把父親安頓了。一天之后父親就在那坡頂安家了。
父親走后,母親告訴我,“國送”是父親給我起的名字,他說他這輩子不能送我讀書了,讓我好好努力,將來讓國家保送。可惜,后來的我不爭氣,沒能讓國家保送,再后來我就改叫國頌了。
第二位父親叫羅寶基,在我8歲他37歲時我們走到了一起,他在我們這個家待了23年。
父親病重時,我從縣城請假回老家照顧他。那幾天,父親一直躺在我身邊那塊臨時搭的床板上。他的皮緊包著骨頭,每一條筋脈清晰可見。
早在幾個月之前,母親給我打電話,說她做了個夢,夢見自己趕集歸來卻找不著家,原來家在的地方只留下一片空空的新地……母親說:“看來今年我或你父親要走了……”當時我喝住母親:“你瞎說什么!”
因為我向來不信夢,還因為那時我剛送走我的岳父。所以對于母親的話,還有她做的夢,我不相信,不想也不敢相信。然而讓我措手不及的是,就在兩個月之后,父親因為身體不適,隨我到縣人民醫院檢查,檢查的結果居然也是食道癌,而且是晚期!和岳父一模一樣的病!而且縣人民醫院已經拒絕開任何藥物了!
從發現病情到我回老家還不足4個月的時間,可父親已經兩個月無法進食了。剛發現時,我告訴他只是食道發炎,吃吃藥打打針就好。除了弄些中草藥,我還自己跑到藥店去買些消炎和保健的藥,把所有商標都撕掉,自己用紙糊上,寫上一天幾次一次幾片之類的話,交待他按時服用就好,他似信非信。那時正值家里谷子揚花,父親還整天硬撐著在田里轉,看哪里水少了放一點,哪里有雜草了扯一下。母親說,因為一天天進食困難,晚上父親時常一個人在那里嘀咕著:現在還整天看護著這兩塊田,也不知道還能不能吃得上……
谷子收時,父親真的連一顆也沒能吃得上。原本和我一樣高、體重比我還重的他,躺在我身邊如一芥草,一不留神就可能會飛走了。
食道癌的晚期,不但不能進食,而且還會不停地出冷汗、嘔吐。那幾天里,我和弟弟妹妹一直拿著紙巾守在他身邊。在給他擦汗擦口水時我不敢正視他的臉,我不忍看到那絕望的眼,我需要不停地動作才能抵得住我隨時要洶涌而出的絕望,才能保持我一如既往的堅強的表情。我知道,我不能沉重,我太沉重了弟弟妹妹會哭,他們還小,他們需要一個堅強的大哥。我太沉重了母親會承受不起,當她的兩個男人都以近似的方式離去的時候,她需要一個人幫頂著,哪怕一點點。所以,我只能一種表情,一種淺淺的憂慮,只能是淺淺的。
母親告訴我,父親就快挺不住時曾交待說:“家里的谷子應該夠安排我的后事了,別搞太浪費,家里有三頭豬,雖然小,殺兩頭就行,留一頭過年了你和孩子們殺了吃。我不在了,你就別待在這房子了,去和孩子們住吧……”
父親走后,我把母親接到縣城一起住,兩年后弟弟有了小孩,母親去宜州幫弟弟帶小孩,兩位父親就永遠地留在老家了。
我時不時會回老家一趟,每次回去,我總會到父親的墳邊看看,每次看到那兩堆已長滿雜草的黃土,我總會想起那首詩:
前天,放學回家,鍋里有一碗油醬飯。
昨天,放學回家,鍋里沒有一碗油醬飯。
今天,放學回家,我自己做了一碗油醬飯放在父親的墳前。
我轉過頭,淚如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