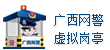雞事三疊

□ 覃寶亮
那年大年初一,青灰色的晨光剛灑滿山村,吊腳樓里就飄出裊裊的炊煙。父親買來一拃長的鞭炮被我凍得通紅的小手點燃,瞬間在屋前炸響,空氣中彌漫著過年的氣息……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大年初一能殺一只肥雞是一家人最體面的一件事。記得有一年,我家幾只土雞剛進入愣頭愣腦的育成期,這樣的雞哪能上桌?不同的是,大伯正提著一只鬮雞來到吊腳樓的石階上,雞咯咯地叫。姐姐攥著我皸裂的手,像看一場電影一樣,跑到大伯身邊,蹲在石階上看大伯操弄。我和姐姐低聲談論最想吃哪部位的肉,仿佛一盤冒著熱氣的白切雞肉已擺在眼前。
那時,我和姐姐都才是幾歲的小孩。我們以為,那只雞也有我們的份。哪想到,老輩傳下的規矩像鐵鎖鏈:初一不討食,不贈肉,防著整年漏財。看著大伯的鬮雞準備下鍋了,父母卻三番五次地叫我們回去。我們還在那里呆呆地看,直到暮色漫過門檻,父親提著一只小雞對我們說,趕緊回來幫忙,我給你們殺雞啦。
雞毛扒光,那只雞就像父親的拳頭般大。看著眼前自己家的雞,想著大伯家的雞,我們無奈又高興。
晚飯的桌上,除了豆腐青菜就這只小雞了,而這只小雞被切成兩半,一半是我的,一半是姐姐的。我和姐姐把雞肉吃得一絲不剩,連骨頭都要嗦干凈,不留一丁點肉味。這件事成了我和姐姐童年里的笑料,也成了一件難忘的家史,使我對雞有一種難以割舍的情懷。
多年后,我來到縣城,又居住多年。后來,我有了一處自建房。我在樓頂有一個用木條自制的雞籠,我在籠子里養雞。
雞飼料是自己配制。每天清晨,這些金黃色的小生靈總在食槽前撲棱起細碎的陽光,啄食的節奏像雨點擊打芭蕉葉。它們個頭一天天長大,羽毛光亮。成年后的雞食量大,我每天投喂兩次。為了不浪費,每次投喂的飼料只夠它們吃半飽——吃多拉得多。還有人傳授訣竅,說餓著點的雞才肯下蛋。正因為這樣,每當我拎著食盆推開鐵門,它們聽到鐵門的吱呀聲,仿佛士兵聽到沖鋒號一樣地往前沖,爭搶著擁擠到食槽前,搶在前面的雞的脖頸如彈簧般伸入食槽,像在彈奏大地一樣啄食,搶不到食物的雞也伸長脖子喙尖雨點般叩擊我手中的食盆,把人的手也啄了一下。它們鮮紅的冠子像跳動的火焰,火焰里藏著生命蓬勃的韻律,讓我有一種六畜興旺的成就感。
無疑,樓頂養雞是解饞使然。長大了的雞,一只只被從籠子里提出來,變成餐桌上的美味,雞籠逐步出現空缺。一段時間,雞籠里的雞只剩不到一半。有一天,我照常提著飼料打開樓頂的鐵門,當熟悉的開門聲再度響起,它們不再振翅奔來,反而瑟縮著退往墻角。雞籠里一點動靜都沒有,我以為發生雞瘟或什么了,可我走到雞籠前用棍子去撩,個個像被捉住一樣往里鉆。當我抓住其中一只雞的腳爪時,另一只突然發出尖厲的啼叫——那聲音不像家禽,倒像是從莽莽山林里傳來的,某種原始而悲愴的呼喊。我無奈地關好鐵門回到屋里。
年復一年,我仔細觀察屋頂上雞群的反應。起初,雞群如出一轍地活躍,即使第一只被我捉住雙腳拉出雞舍,鐵門照常開啟時,剩下的仍在埋頭搶食,全然不知宿命的來臨。直到食槽前的身影悄然減少,某種微妙的變化開始在羽毛間涌動,仿佛懂得計算人類的腳步聲。它們不再用喙叩擊雞籠,不再將翅膀拍打得簌簌作響。當熟悉的腳步聲再度響起時,它們像被施了定身咒的雕塑,在晨光里縮成灰撲撲的一團,黑豆似的眼睛突然噤聲。它們終于感覺到門縫開合之間意味著什么,因此學會了沉默,就像無聲的抗議。
撼動我對雞生命的認知,是一只陪伴家人13年的公雞。2011年冬月的夜晚,母親離我們而去。給母親守靈,除了親屬和朋友,還有一只雄性十足的公雞。按當地風俗,公雞被賦予了重要角色。這只公雞不能殺,我們留它守家,任由生命走到底。我哥就在自家樓頂放養著,從此它成了樓頂的活祖宗。
2023年,還是一個寒氣逼人的夜晚,離春節就剩兩天,父親拋下我們走了。也許是母親在等他。辦理父親的后事時,我哥把樓頂的活祖宗帶到父親的靈堂,鄉鄰們像看天外來物一樣圍觀籠里這稀世的“老壽星”,無不嘖嘖稱贊。它喙尖得像鋒利的彎鉤,雞蹬子形似牛角長到三寸多長;在賓客雜沓的腳步間,它悠閑地啄食,不忘報曉,小孩手掌般大的冠羽在穿堂風中微微顫動。送走了父親,我哥仍把它當活祖宗一樣伺候,直到它生命的終結。
雄雞兩次守靈,像是父母在輪回里的一次對視,借由這羽族的身軀,完成對人間最后的眷戀與告別,讓每個生靈都能在屬于自己的故事里,成為被記住的存在。